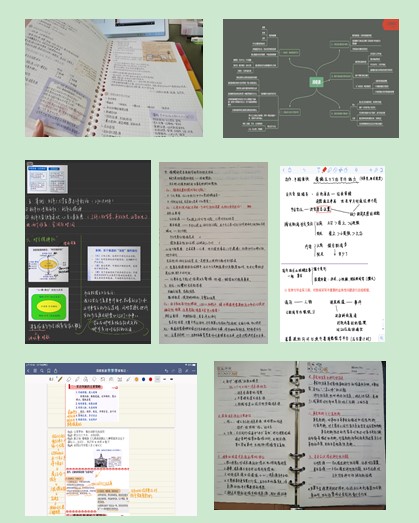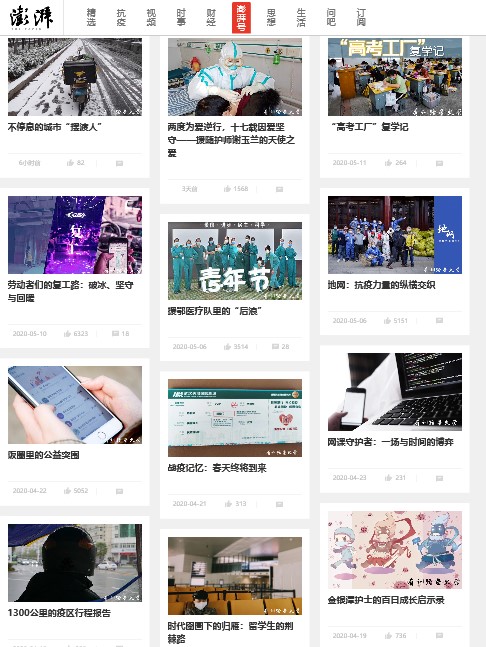在南方报业传媒的“记疫2020X城市记忆计划”活动的比赛页面里,入围决赛的13篇文字作品中有6篇来自南昌大学,在澎湃湃客专栏下,有12篇标示为“有训路星火营出品”的报道获得了近5万的点击量。 这些报道都与当下疫情有着紧密联系,虽然文章落款都是四五个不同的名字,表明这是一篇多成员合作完成的报道,但他们都有着同一个指导老师——刘琳。 一门因为疫情临时转入线上教学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群因为疫情连小区大门都出不去的大学生,是如何在刘琳老师的带领下,炼成这一疫情系列报道? 网课建设:克服线上线下的落差 2019年的圣诞节,校园里到处是节日主题的装饰品,因为正值秋季学期的最后一个教学周,老师们也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和家人一起感受冬夜的悠闲。 刘琳老师却开始了下一个学期的教学准备,“我教采写业务课程十多年了,我知道学生们在课堂讨论的每一个反应,传统教室的布局限制了团队沟通,我早就想换个方式”,她说的这门课程,是新闻专业的核心课程《深度报道》,为了打破传统教室的空间限制,她准备申请智慧教室,但申请的前提是——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教学形式的改变意味着她要对课程教学做出全盘调整,“最大变动是要删减20%的理论教学内容,增加实践讨论的比重,而这个环节的时长、节奏最难把握,既不能为讨论而讨论,也不能因讨论而影响课程整体进度”,整个1月份,刘琳老师一边修改理论课件,一边反复研究课程练习、项目的可行性,“我甚至想好了各小组举着小黑板抢播新闻的场景!” 然而,2月4日教育部一纸《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把刘琳老师对“翻转课堂”的种种设想变成了对网课会否成为“翻车现场”的深深担忧。 “距离开学连半个月都不到,要根据网课特征再设计一版教学方案,不清楚呈现界面,不了解平台设置,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倍感压力,网络教学咨询群的消息任何时候打开都是99+的状态,大家都在恶补技术短板”。不过对于刘琳老师来说,网课更具体的痛点还是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带来的落差,隔着屏幕的教学“找不准说话的节奏点”,打乱了老师讲解业务的即兴发挥,“面对面的那种通过眼神、肢体产生的情理互动也被阻滞了”。 根据学校的教学指导意见,老师们纷纷从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中搜寻教学资源,刘琳老师也坚信“从国家精品课程里选出的慕课资源,肯定比自己仓促弄出的PPT+语音要精彩多了”,但在选择慕课资源时,她发现现有的慕课资源以史论课程居多,新闻实务类的课程在同专业课程的占比还不到10%。从视听感受来说,新闻写作课程的慕课情节丰富、节奏紧凑,但产量还不及中文、法学等专业的写作课程,这个现象给了刘琳老师很大的警示。“我很好奇,只能自己找答案,把能找到的新闻写作类慕课都先看一遍”。 2月19日,《深度报道》课的89位学生在学习通上收到了刘琳设计出的网络版教学方案:慕课先导——主题强化——实践检验。“听着过瘾、过目就忘”是刘琳老师亲身体验慕课学习后的感受总结,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她一幅幅梳理出慕课的知识图谱,围绕重点内容设计讨论、作业,然后根据学生的发帖数量、测试题的正确率、作业反馈情况来筛选难点,制作专题讲解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我得找到你们的节奏,不能指望视频带着你们一路狂奔,以学定教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回接触大规模网课的学生,对这门课的节奏紧追慢赶,慢慢适应了每周的课件测验讨论题作业模式。即便没有笔记的考核要求,但学生们有的用手账,有的用思维导图,还有的用传统的方式把知识点整理成整齐的笔记。 图1 新闻系学子在学习通晒出的笔记 疫情采写: 新闻理想在笔下发光 “没有采写任务的新闻业务课就是耍流氓”,刘琳对每届学生都笑着提过这句话,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课程的影响不仅是线上内容的重置,还关系到线下活动能否开展。 “大四的毕业实习都因为疫情临时更改了考核方式,我还捣鼓着怎么把学生轰出去采写”,这个逆流而上的决定,其实是刘琳思虑许久才做出的。在《南都周刊》深度训练营的访谈中,她把做出决定的缘由归为李文亮事件后的舆论风潮,“学生们开始怀疑善良,怀疑信仰,怀疑自由,同时还有一股从对现实到对媒体的失望汹涌而至,从疫情开始前就一直在涌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绪裹挟下,如何去开掘新闻的意义?如何让孩子们相信信息传播的正向力量?如何让他们还愿意拿起手中的笔去记录去反思? 回避这些的话,我所有的教学便是无用功。” 为了让教学形成“有用功”,刘琳说她把“最美人间四月天”过成了“爆肝改稿四月天”。 《来点深度》小组报道的是疫情中艰难求医的肿瘤孕妇,他们在朋友圈发现一则某大病筹款平台上发布的启示,于是联系了患者的丈夫并获得了19138字的采访记录,但是在写稿环节,采访对象因为担心报道影响生活而态度大变,组长说:“当我们还抱着希望的时候,采访对象连发五个道歉红包。那一刻,感觉自己被击倒在道德洼地。”接下来和采访对象的互动策略、稿件走向,都在刘老师一路指点下逐渐明朗,最终《1300疫区行程报告》出炉。 另一个小组中,刘琳光是选题会就参与了三轮,几番“推倒-重来”后终于锁定采访对象为疫情中的留学生,而刘琳又对信源的广泛性、典型性提出了要求,她一边“逼迫”组员们扩大采访面,一边倒着时差自己同步采访。 报道疫情期间学校网课平台建设的小组,初稿几乎被全盘推翻,刘琳又主动和部门领导沟通,为小组采写获取更多素材,最终稿件在中国江西网发表。报道党员医生的小组放弃了采访对象观点和评价过多的一稿,在刘琳老师的指导下几易其稿,最终也在澎湃号上发表了。 图2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寄来的获奖证书和奖品 记者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几乎每个小组要经历最少三轮修改,每篇文档字数不下5000,每段批注不少于20个字,每次腾讯会议短则半个小时,每条微信语音留言50秒以上……这些数据,后来演变成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疫情征稿活动的6个一等奖,澎湃湃客专栏的12篇报道,连刘琳老师自己都难以置信。 对于新闻系的学子来说,关于疫情的报道如雪花纸片一样纷沓而至,有一部分曾经误伤了他们心中的新闻理想。但当他们加入疫情报道的战场时,这群孜孜不倦向信源求证、多番修改补充报道细节的学子,不可不谓没有怀抱一定的信念、一定的激情在报道疫情,他们的笔下一定闪动着理想之光。 终有所获:在报道疫情中共同成长 明代学者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写到:“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宋濂一定不是最笨的,对“故余虽愚”的理解或许可以往对知识的敬仰上走。而对于新闻系的学生来说,疫情期间,他们在一个没有监督、没有外力帮助的环境下完成十余篇报道,并由此催生了“有训路星火营”——一个立足于澎湃号的深度报道训练营,成为了他们额外的收获。 在刘琳老师看来,“深度报道最初的本意,是教会学生追寻新闻更深层次的含义。在这个意识的引导下,把学生遇到的一些常见业务问题做一个总结”,但十年来的教学实践里,刘琳发现学生真正地成长并非“技”的提升,“新闻采写是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则、有大量成功优秀的经验,但它归根到底是‘人学’,要靠‘道’的修炼才能笔下生花”。 这里的修炼,是对师生双方而言的,刘琳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学生成长的守望者,她说“很贪心地想要和学生一同成长,我希望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我能够让你们兴奋起来,你们也能给予让我兴奋起来的回应。新闻采写是个千人千面的过程,我的认知也会因为你们而改变”,尽管学生的作品硬伤累累,但这并不影响她“照出自己身上种种得与失”。 “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最大的魅力,也就是在于此。它不是传授你一个具体的技法,而是传授你一种以后生活当中,你会一直在精神里面坚守的一种意识”。 这和陶行知关于教育的论述“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3 有训路星火营澎湃号上发表的疫情报道 正如此番课堂里的十余篇疫情报道,师生一起从金银潭护士的三次哭泣里去体会被迫成长的滋味,跟随1300公里的疫区行程报告去感受生死赛跑的紧张,连线英美俄法的留学生去品味中国青年身上延续百年的奋斗精神,见证学习通管理团队传递科技的温暖之光,洞察饭圈规则下粉丝公益的巨大潜力……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共同构筑了对这场疫情的特殊记忆。 江丽/文